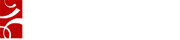2014/11/21-12/28 北師美術館
2014/11/21-12/28 北師美術館

無分古典與當代、傳統或現代,藝術家終其一生,盡在處理對於企及探索或挖掘自我的渴望;而人類終其一生都在處理協定、許諾、誓約,用履約和實現的結果來回憶或是評價誓言那一刻的永恆價值。
作為一個「人」的藝術家,又怎樣看待「誓言」與「逝言」?
北師美術館館長林曼麗所秉持跨域和實驗的當代精神想像,邀請了姚淑芬進行策劃,她思索了王攀元生涯面對的孤獨與流離,以及那段牽絆一生的許諾話語,在和策展人吳牧青共同發想與結構概念後,將「誓言、消逝、話語、流動與永恆
」作為互為交織對話的核心,形成「誓.逝 Eternal Fading Words」中英文不對稱的計畫命題。

誓言是一種最具語言定向強度的命名,並力促著起誓或被給出諾言的自我在大他者的眼光成為圖畫(Picture),以天地為證,或有他人在場:在愛情中,這個他/她者,則是給出允諾或收下誓約的愛人。王攀元畫畫,畫的是對於當年她對他誓言的追憶,畫的也是自我現今的寫照,但此種力求成為圖畫去表徵誓言的最終極處,是否是作為當代藝術的終極目標所在?
在國北師美術館《誓˙逝》一展裡,此目標卻正好是對此圖畫/誓言的解構與消減,姚淑芬舞者的肢體行為和吳牧青策展藝術家們的藝術裝置,之所以多了一層不只是向王攀元致敬的迴旋餘地,是因為展覽總預示了誓言之破滅,而當誓言成為逝言時,圖畫也才有了重回基進處的可能。所有誓言的收回或收不回,所有逝去之誓言的回收或不回收,皆是從成為圖畫的慾望中撤退,於是我們可以得見更多更為生動的演示,一個個專屬於活人畫(Living Picture)乃至於更甚的圖景(Tableau)。



- 參展藝術家
 王攀元、姚淑芬、李明學、秦政德、鄧泰華、Leisa Shelton、Jeroen Speak、Keisuke Takahashi
王攀元、姚淑芬、李明學、秦政德、鄧泰華、Leisa Shelton、Jeroen Speak、Keisuke Takahashi - 釘子藝術家
 蔡明亮
蔡明亮 - 客席表演者
 劉守曜
劉守曜 - 共同策展
 姚淑芬、吳牧青
姚淑芬、吳牧青 - 表演者
 李蕙雯、陳維寧、洪紹晴、田孝慈、劉家瑞、李宗霖、宋宜倩
李蕙雯、陳維寧、洪紹晴、田孝慈、劉家瑞、李宗霖、宋宜倩 - 視覺指導
 李明學
李明學 - 特別感謝
 王攀元
王攀元 - 平面攝影設計
 劉悅德
劉悅德